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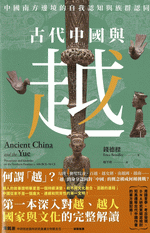 |
古代中國與越: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錢德樑 著 賴芊曄 譯
|
|
| 出版社:八旗文化 |
| 出版年:2022年11月 |
| コード:484377 325p 23cm ISBN/ISSN 9786267129975 |
| |
|
|
在庫僅少
弊社の在庫が2,3部以下のものです。店頭在庫については別途お問合わせください。
|
|
|
|
|
|
「越」とはいったい何か。
「呉越」の「越」、古代諸族「百越」の「越」、「越南」の「越」
春秋の古代からベトナムの近現代に至るまで、中国大陸の南方に存在したいくつかの「越」と呼ばれる国家や文化群について、言語学的研究や考古学的発見等の最新の知見を駆使しながら分析研究した一書。
古代中原地域から「野蛮人」と見做されていた南方諸民族の個々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や、現代中国南部や台湾、東南アジア地域に残る諸言語のルーツを解き明かしていく。
●著者紹介
錢德樑(Erica Fox Brindley)
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東アジア学にて博士号取得。現在ペンシルバニア大学アジア学研究科主任、および歴史学哲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化史専攻。
著書に『古代中國的音樂、宇宙學與和諧政治(原題Music, Cosm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Harmony in Early China)』(暫訳)(2012年)および『古代中國的個人主義:人的代理與思想政治的自我(原題Individualism in Early China: Human Agency and the Self in Thought and Politics)』(暫訳)(2010年)等あり。
本書『古代中國與越: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は、原題を『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 Perceptions and Identit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c. 400 BCE–50 CE』といい、ケンブリッジ大学出版より2015年9月に出版されている。
●訳者紹介
賴芊曄
台湾の政治大学歴史学科世界史修士。翻訳書に『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原題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著者David W. Anthony、『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原題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著者Sanping Chen(以上八旗文化より出版)等あり。
●推薦者紹介
黃銘崇
台湾の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文物館主任。中国古代史専攻。
ハーバード大学東アジア学にて博士号取得。『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6)や『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等を編纂。
何謂「越」?
重新解讀史料、結合語言學與考古學,第一本深入對越、越人國家與文化的完整解讀!
「越」的身分認同,對「中國」的概念構成何種挑戰?
越人的故事又是如何證明──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龐大、連續和同質性的單一文明!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文物館主任――黃銘崇 導讀推薦※
在現今許多人的認知中,「吳越」文化是「華夏」文化的一部分,是非常順理成章、毋庸置疑的概念。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也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中最勵志的道德傳奇故事。然而另一方面,現今我們一聽到「越」(Viet),腦中會立刻閃過越南人及其歷史與文化,並不會立刻與歷史上的「吳越」、「百越」產生聯想,彷彿兩者之間沒有關係。這又是何故?
何謂越?越人又是誰?越人和中國人之間又是何種關係?本書可謂是首次全面、深入地分析「越」這個漢字標籤背後所隱藏的歷史真相。透過作者錢德樑(Erica Fox Brindley)的精彩研究,解答了很多與越相關的歷史文化上的疑問。
◆「越人」這個群體所講的語言,到底是接近於現今台灣原住民的南島語,還是現今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所講的南亞語?或是中國境內的苗瑤語?
◆春秋戰國時期,「越」還被中國人視為野蠻人,為何到了東漢時期,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故事卻被中國視為理想的道德典範?
◆被髮、斷髮與紋身這些今天的國際時尚,是古代越人的象徵標誌。古代中國人如何記錄、看待越人的這種身體語言?
◆金庸小說《越女劍》書名借自東漢中國的野史傳說,華夏知識分子究竟出於何種心理,把越人、女性和鋒利的寶劍聯繫在一起?
◆漢代位於廣州的南越國,其太后樛氏的真實身分,是漢廷派往南越的女間諜嗎?南越的亡國是她的政治目的嗎?
◆阮朝將國號定為「南越」,為何被清代的嘉慶帝改為「越南」?順序的前後改變意味著什麼?
要真正理解中國史或東亞史,就無法迴避「何謂越?」這個重要問題!因為越人或越文化的歷史,涵蓋了今天中國長江以南到越南北部的廣袤南方地理景觀。不僅僅包括東亞沿海的浙江、福建、廣東和廣西,還包括江西、湖南和西南部的雲貴。可以說整個中國本部的一半,都是越人的活動空間。
生活在中國南方邊境的「越」,他們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是什麼?這個極其關鍵的問題,卻向來淹沒在中國大一統歷史敘述中,很少被探究和分析。本書研究指出,「越」這個漢字詞彙所涵蓋的各色人群,不一定認為自己就是「越」!「越」不是自稱、身分認同或本名,而是古代中國人對南方原住族群的他稱和總稱。此外,越也並不限於表達單一的族群或文化。所謂的「越」本身,其實是一個多國體系。
如何突破中國文獻的偏誤和局限?本書的獨到之處是充分利用了考古發現和語言學證據。雖然越南考古學家所說的越,和中國考古學家所稱的吳越、閩越、百越,都各自投射了不同的民族主義立場,試圖把考古發現的解釋指向自己的國家。但是,作者認為,古代詞彙中的「越」,或現代考古文化中的「越」,又或者在「幾何印紋陶層位文化」及「原始南島語系群體」這類的標籤之下,也從未反映出任何統一的概念。即一個統一的「越」是不存在的。
語言學的分析也證明這一點。假定讓吳國滅亡的美女西施真的存在(這是東漢中國人編造出來的野史),那麼西施講的是何種語言?作者專闢一章來分析越人的語言,得出結論:越人講的語言可能接近今天的南島語(台灣原住民)、侗台語(今天的泰國話、寮國話)、南亞語(今天的越南語)或苗瑤語(今天的苗族、瑤族語言),但不是漢語。
這是本書最令讀者感到洋溢著魅力的地方,也是本書最為精彩和核心的論述──錢德樑認為,儘管長江以南的各族群共享某些文化或文明,但「越」從來不是一個整體、一個國家、一個語言族群。中國知識分子記錄中的整體的、單一的「越」,掩蓋了它們真實的族群多樣性。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作者分析說,最根本的原因出自中國人的宇宙觀。中心性(centrality)和居中性(centeredness)的邏輯觀念將華夏自我與地理上的中心綑綁在一起,因此形成了「華夏」和「中國」這種單一、統一的身分認同。而在「華夏中心」的眼中,「越」變成一個具有同一性的「他者」。從上古的記載,一直到帝制初期(秦漢)的司馬遷的筆下,華夏知識分子的目的從來不是實證性的、人類學的研究,而是借助各種修辭、儀式和標籤來「銘刻越」,志在「展演華夏」(本書第三部的名稱)。
所以,從認為越人「其民麋鹿禽獸」,到勾踐變成了中國人勵志復國的道德楷模,中國文獻中的「越」,實際上更多是越文化在華夏文化中的想像與轉化。反之,結合語言學和考古發現,越人的故事也呈現出一種以「漢本位」的視角建構中國身分認同的方式,反過來證明了「中國」不是龐大、連續和同質性的文明。
|
|
|
|





